
在郑振铎的批判视野中,武侠小说的流行事关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他站在革命者立场上,找到了武侠思想和国民劣根性的联系,对武侠小说进行了深刻批判和全盘否定。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郑振铎的侠文化批评话语具有积极的实意义,但也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局限性。
郑振铎曾是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关注现实的社会和人生问题,反对游戏的、消遣娱乐的文学观,坚持艺术为人生的主张,注重文学的社会功利性。在对待武侠小说的态度上,他找到了武侠思想和国民劣根性的联系,站在革命者立场上,从挽救民族性格、拯救国民灵魂的高度,对武侠小说进行了深刻批判和全盘否定。
在《论武侠小说》中,郑振铎把武侠小说的流行视为关系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的大事,开篇就旗帜鲜明地指出:当今之事,足为“人心世道之隐忧”者至多,最使我们几位朋友谈起来便痛心的,乃是,黑幕派的小说的流行,及武侠小说的层出不穷。这两件事,向来是被视为无关紧要,不足轻重的小事,决没有劳动“忧天下”的君子们的注意的价值。但我们却承认这种现象实在不是小事件。大一点说,关系我们民族的运命;近一点说,关系无量数第二代青年们的思想的轨辙。因为这两种东西的流行,乃充分的表现出我们民族的劣根性;更充分的足以麻醉了无数的最可爱的青年们的头脑。
在这里,郑振铎把武侠小说和黑幕派小说相提并论,并称为最使人痛心疾首、关系民族命运的大事,不仅表现出了民族的劣根性,更足以麻醉青年们的头脑。正是在这种清醒的理性认识指导下,他深深感到“为了挽救在堕落中的民族性计,为了‘救救我们的孩子’计,都有大声疾呼的唤起大众的注意的必要”。进而,郑振铎把斗争矛头指向了清末的武侠热:
像《施公案》、《彭公案》、《三侠五义》(即《七侠五义》之原名)以及《七剑十三侠》、《九剑十八侠》之类。他们曾在三十年前,掀动过一次轩然的大波,虽然这大波很快的便被近代的文明压平了下去—那便是义和团的事件。但直到最近,他们却仍在我们的北方几省,中原几省的民众中,兴妖作怪。红枪会等等的无数的奇怪的组织,便是他们的影响的具体的表现。
郑振铎把义和团运动中所表现出来的愚昧迷信和破坏性看作清末武侠热造成的恶果之一,也把当时红枪会等民间组织的“兴妖作怪”作为武侠小说影响的具体表现,这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揭示以武侠小说为艺术载体的侠文化的负面作用和消极影响。就义和团运动而言,武侠小说中所渲染的侠客、剑仙的超人武功和神奇法力以及刀枪不人的特异功能等愚昧迷信的内容,经过造反首领的改造,对下层民众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和诱惑性。下层民众加人义和团,在“扶清灭洋”旗号的鼓动下,凭着朴素的爱国热情,以血肉之躯抵抗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掀动过一次轩然的大波”,最终的结局却是不仅没有打败洋鬼子,反而落得个为清王朝利用之后反遭剿灭的可悲结局。在诸如此类的事件中,“不知有多少热血的青年,有为的壮士,在不知不识之中,断送于这样方式的‘暴动’与‘自卫’之中’。义和团运动的原始反抗最终敌不过以西方坚船利炮为象征的近代文明,在“扶清灭洋”的斗争过程中,确实也表现出了迷信的短见和愚昧的匹夫之勇,这是侠文化发展到近代以后所暴露出来的负面作用,也是郑振铎以启蒙主义立场对侠文化弊病的深刻洞见。这是值得肯定的。
在郑振铎看来,武侠小说对于民族的危害是非同小可的,必须加以警惕和注意。在揭示武侠小说发达流行的原因方面,郑振铎指出:
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便是一般民众,在受了极端的暴政的压迫之时,满肚子的填塞着不平与愤怒,却又因力量不足,不能反抗,于是在他们的幼稚心理上,乃悬盼着有一类“超人”的侠客出来,来无踪,去无迹的,为他们雪不平,除强暴。这完全是一种根性鄙劣的幻想;欲以这种不可能的幻想,来宽慰了自己无希望的反抗的心理的。武侠小说之所以盛行于唐代藩镇跋危之时,与乎西洋的武力侵入中国之时,都是原因于此。
郑振铎通过分析读者的接受心理,既找到了武侠小说发达流行的原因,又找到了武侠思想和国民劣根性之间的联系。无力反抗强权暴政的民众在现实中找不到出路,而武侠小说中除暴安良的侠客能够激起他们内心被拯救的渴望,在阅读中他们孤独无助的心理会得到宽慰,但他们也极易陷人不切实际的幻想,丧失自主命运的斗争精神。郑振铎对读者接受心理进行分析的深层目的在于,希望深受武侠思想毒害的广大民众能够放弃一切不合实际的幻想,真正地自主命运,起来反抗阶级压迫,带有阶级斗争的革命色彩。在郑振铎看来,武侠思想是谬误的有毒的,是麻痹和腐蚀民众斗争意志的精神鸦片,武侠思想既助长了民众漠视现实斗争的心理,又深人国民灵魂,造成自我麻醉、安于现状而怯于抗争的国民劣根性。由此郑振铎深人反思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对武侠思想批判的不彻底性:
当时,虽然收了一些效果,但可惜这些效果只在浮面上的,—所谓新文化运动至今似乎还只在浮面上的—并未深入民众的核心。所以一部分的青年学子,虽然受了新的影响,大部分的民众却仍然不曾受到。他们仍然是无知而幼稚的,仍然在做着神仙剑客的迷梦等等。
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进行了历史清算和价值重估,对侠文化(武侠思想)也进行了清理和批判,但实际效果并不理想,五四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任务远远没有完成。郑振铎结合1930年代的武侠热,列举了许多当时《时报》的本埠新闻所报道的少男少女们弃家访道的故事,《时报》记者认为这些少男少女们都中了武侠小说及电影之迷。同时指出当时的小学教科书也充满了武侠思想。可见,武侠小说在当时的影响是相当普遍的。从而把批判的矛头又指向了现代武侠小说。在郑振铎的批判视野中,武侠小说所散布的武侠思想“使强者盲动以自找,弱者不动以待变的。他们使本来落伍退化的民族,更退化了,更无知了,更宴安于意外的收获了。他们滋养着我们自五四时代以来便努力在打倒的一切鄙劣的民族性”尸在郑振铎看来,武侠思想对民族的未来发展遗害无穷,他对武侠小说的作者们、出版家们以及武侠电影的编者、演者们也提出了质问,警告他们注意武侠思想的负面作用和消极影响。最后出于继续进行思想革命的需要,郑振铎认为五四时代并未完全过去,他呼吁:“我们正需要着一次真实的彻底的启蒙运动呢!而扫荡了一切倒流的谬误的武侠思想,便是这个新的启蒙运动所要第一件努力的事。可见,在对清末武侠热有了清醒的理性认识,并且在深刻反思了五四思想革命对武侠思想批判的不彻底性,以及正视现代武侠小说普遍流行的基础上,郑振铎大有在思想文化领域内开展“二次革命”的决心和毅力。而把扫荡武侠思想作为新的启蒙运动的第一件努力的事,足以体现出郑振铎对待侠文化和武侠小说的无情批判与彻底否定的文化态度。
在《我们所需要的文学》中,郑振铎结合“九·一八’,和“一二八”事变后中国人民开始了民族抗战的大时代,把武侠小说视为应该无条件斥责、扫荡和打倒的不良的文学,郑重地指出了武侠小说的危害:
武侠小说的发展与流行,害苦了一般无充分识别力的儿童们;那一批躺在上海的鸦片烟榻上的不良作家们,在他的随了一圈圈的烟圈而纠绕着的幻想里,不知传染了多少的清白无辜的富于幻想的小儿女们。报纸上所记载的许多弃家求道的男女儿童们的可笑的故事,便是他们的最好的成绩!
在郑振铎看来,武侠小说毒害着少年儿童们的心灵,对青少年的成长有着严重的误导作用。这样的小说不利于“九一八’,和“一二八”事变后的伟大时代的斗争。他认为,“五四”是一个普遍的思想界的反抗时代;“五册”是一个更伟大的一部分青年以实际行动起来反抗的时代,也就是革命作家放下笔杆子、拿起枪杆子的时代,等革命高潮过去后,他们又拿起了笔杆子;“九一八”和“一二八”事变后的时代与以前不同,真实的经验,真实的行动,真实的反抗,真实的斗争,使他们更深刻了,更热情了,更伟大了。在抗日救亡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文学应该有个更伟大的前途:
在这热烘烘的,火辣辣的伟大时代里,正是伟大文学的诞生的最适宜的时期。在真实的生或死的争斗的火光里,照见一个伟大的文学的诞生,而呐喊、冲锋、炮弹的炸裂便是诞生的贺歌。而广大的群众也正在等候着。是起来的时候了,亲爱的作家们!抬起头来;无垠的地平线上广大的群众在当前。
“九一八”和“一二八”事变后,抗日救亡开始成为重大而统一的时代主题,一切文艺活动都应该无条件地服从抗战大局,这是革命作家的一贯立场。郑振铎正是从革命者立场出发来审视武侠小说和呼唤与伟大时代相合奏的伟大文学的。他对武侠小说的批判及对伟大文学的呼唤,有利于唤醒沉溺于武侠思想中的民众的民族意识和反抗意志,鼓舞他们积极投身于抗战的洪流。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郑振铎的批判侧重于文化启蒙,具有反封建思想革命色彩、阶级斗争的革命倾向和反帝救亡意识,他的侠文化批评话语适应了时代的需要,充满了历史的文化的反思和感时忧国的人道情怀。但在对待侠文化和武侠小说的态度上,“过分强调小说的教诲功能而完全否认其娱乐色彩,并进而从思想倾向上全盘否定武侠小说’却是有失偏颇的。我们肯定郑振铎的侠文化批评话语具有历史的合理性与时代的进步意义,但对其局限性也必须保持清醒的认识。
“武侠小说其实只是小说的一个品种,而不是一种固定的思想倾向。虽然一般武侠小说都肯定行侠仗义,急人所难,但就具体作品而言,内容比较复杂,有的突出除暴安良,有的渲染血腥复仇,可以说全由作者思想高下而定。因此,对于侠文化或武侠小说的评价决不能一概而论,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根据每部武侠小说的具体情况来为其定性,决不能因为某些武侠小说的思想倾向存在封建糟粕,而对作为一种文学类型的武侠小说乃至侠文化从整体上作出危害社会和人民的结论。正如陈平原所言:“武侠小说作为一种通俗艺术,首先考虑的是如何才能被广大读者接受并转化为商品,而不是传播哪一种思想意识。指责作家有意毒害青少年,或者赞扬其弘扬爱国精神,其实都不得要领。我们应该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
摘要:艺术的国际性同样处于发展之中,保持艺术的民族性不能夜郎自大和无视他民族艺术精华。我们应不断吸收他民族艺术的精华,以完善和发展本民族艺术,民族性在世界艺术的大舞台上才有意义,离开这个舞台不仅其艺术的民族性将失去光彩,艺术的国际性也不复存在。关键词:艺术民族性国际性对立统一 一、艺术的国际性与民族性及其关系 艺术的国际性主张摆脱桎梏、解放思想、抛弃民族文化传统,是一种超阶级的势力扩充...
人们在歌唱时的状态很多,有呼吸状态、发声状态、情绪状态等等。这些状态对歌唱都有着重要的作用,它们既是相对独立的,又是彼此相互联系的。可以说声乐是以人体为乐器的,人体就好比是一部大机器,机器是由若干个主体、副件及螺丝打所组成的一个整体。其中每个主副件及螺丝打都起看它应有的作用。人体在歌唱时也一样,人体的各个器官在歌唱时的各种状态,都与歌唱有着直接关系,直接影响歌唱时声音的准确性和科学性,所以分析、理...
文章通过说明在这个艺术与自然联盟的时代,自然韵律美为设计开辟了新途径,着重论述了肌理美在设计中的运用,并结合自己的实践,阐明了肌理美与自然材质设计带来的自然韵律美。1自然韵律的美为设计开辟新途径 1.1艺术将进入与自然的联盟时代 古代人看来大自然是智慧的源泉,是万物的母亲,所以中国古代便有天人合一的说法。但到了近代,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工业社会成了一个把世界拆零了的时代,现代科学的发展,使人们意...
本文通过各种激励方法的分析,阐述在思想政治工作中,正确运用激励,激发职工的意志、挖掘人人内在法力,鼓舞人们奋发向上,充分发挥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以便提高工作效率,更好地做好工作。 关键词:思想政治工作;激励;方法 激励方法是思想政治工作中的重要方法,是开启人们心扉的钥匙。所谓激励,就是激发和鼓励,通过一定的手段和方法,激发人的革命意志,挖潜人的内在潜力,鼓舞人奋发向上的精神。心理学告诉...
改革开放30年来,乡村社会的发展与巨变同时带来了乡土文化的价值冲突和认同缺失,传统乡村文化在农村现代化的建设中遭遇了“破坏有余”和“重建不够”的历史命运。总结和反思现代化背景下乡村文化建设的传统角色及其实际作用和价值,对于乡村社会变迁下的文化发展而言,其核心概念是要树立“文化自觉”的理念,坚持文化传承与文化延展的统一,在开放性...
本文从需要层次理论、激励理论作用及身心发展规律方面,进行了医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中人性化心理学的探讨。医学生是大学生中特殊的群体,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医学生的思想观念及行为方式也都随之发生重大的变化,这就要求对医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决不能仅仅从教育学角度去认识和考虑问题,而是必须在理解人、尊重人、关心人、信任人的基础上从人性化心理学角度去思考和指导思想政治工作,才能与时俱进,收到实效。 1从需要层...
栏目制作方法是提高栏目整体质量的重要因素和环节。活动的主体的选择,解说词与画面关系的处理方法;背景资料的搜集运用和配音配乐选择定位,综合运用,可有效提高栏目质量。随着电视节目的日益栏目化,栏目质量成为决定一个电视媒体得失乃至成败的重要因素川。而栏目质量的决定因素,除了特色定位、形象包装、品牌效应、栏目管理等宏观因素以外,具体的栏目制作方法仍然是栏目质量产生过程的重要环节和因素。同时,电视栏目的组织...
近年来,由于湖南电视、广播传媒事业的飞速发展,出现了大量特有的时尚方言词语在湖南流传。它们具有形象性、通俗性、流传性的特点。反映的内容主要有:(1)反映湖南人交际变化;(2)反映湖南人称呼变化;(3)反映湖南人经济活动变化。它们折射出湖南人求新、求异、从众等社会心理。 近年来,受到湖南电视、广播传媒飞速发展等因素的影响,一些有湖南方言特色的时尚词语非常流行。这些时尚词语有独特的新鲜感和强大的生命...
近年来,由于湖南电视、广播传媒事业的飞速发展,出现了大量特有的时尚方言词语在湖南流传。它们具有形象性、通俗性、流传性的特点。反映的内容主要有:(1)反映湖南人交际变化;(2)反映湖南人称呼变化;(3)反映湖南人经济活动变化。它们折射出湖南人求新、求异、从众等社会心理。 近年来,受到湖南电视、广播传媒飞速发展等因素的影响,一些有湖南方言特色的时尚词语非常流行。这些时尚词语有独特的新鲜感和强大的生命...
文章研究铁凝小说对人物心理透视的多重方式,探寻其作品经久不衰的魅力之源。铁凝时而将激情描述与理性分析融为一体,时而编织多声部的叙述和对话构成多重视角全方位透视人物心理,时而借助人物的外在行动凸现内在运动的轨迹,最终让读者走进人物的心灵深处。 论文关键词:铁凝;小说;心理透视;分析 铁凝的小说已引起广泛关注,对其做出评论、研究的文章不可胜数,多从叙事伦理、第三性视角、人性挖掘、语言风格等方面进行...

影响因子:3.959

影响因子:0.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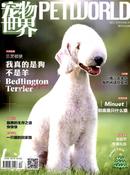
影响因子:0.000

影响因子:1.6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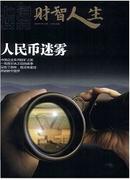
影响因子:0.000

影响因子:0.550

影响因子:8.440

影响因子:0.000